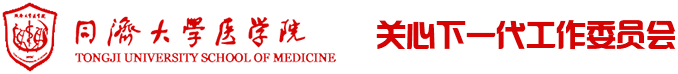
理性民主的讨论是使社会趋近正义的有效手段
来源:同济医学院关工委编辑录入:oy 2013/2/20 11:40:47 1051
来源:文汇报 2013年2月18日第9版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池本幸生
◆池本幸生近年来致力于将印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著作和学术观点介绍到日本国内。在池本看来,日本“311”大地震后危机被人为严重化的状况中也能隐约看到森的饥荒理论的影子。近日,池本教授在复旦大学的研讨会上联系阿玛蒂亚·森《正义的理念》一书中的观点,对日本目前面临的危机加以讨论,并在此期间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本报记者 任思蕴
在2011年,日本东北部发生了震惊世界的“311”大地震。地震引发了福岛核电站事故和日本东北部核危机,但日本政府却避谈灾难的严重程度;此外,由于媒体缺乏对灾区的客观报道,无视政府公告以外的灾区情况,也间接导致一部分海啸袭击地区未得到有效救援。日本政府的虚与委蛇和媒体的片面立场广受批评。
同年,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池本幸生正在翻译印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的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等作品。“311”大地震中危机被人为严重化的状况令他联想到森关于饥荒的理论。虽然一般认为饥荒是因为歉收而导致粮食不足,但森的研究证明,饥荒不仅仅在粮食供给量急剧下降时才会出现,也可能是因为国家的强力干预而使一部分人失去对粮食的索取权,也可能是饥荒发生时部分人未得到关注而得不到国家应对措施的救援。关于饥荒的理论是帮助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研究。在池本幸生看来,日本“311”大地震后的危机中也能隐约看到森的饥荒理论的影子。
经济学家总是很关注GDP的增长,而森对只注重GDP的经济发展观点持批判态度。池本幸生对森的经济学研究取向非常感兴趣,近年来也致力于将森的著作和学术观点介绍到日本国内,尤其关注的是森关于正义和民主的论述。
不久前,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联合主办的第二届FTP三校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三校的20位与会者围绕“世界史/全球史视野中的东亚”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14-21世纪东亚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和国际地位、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东亚与西方的关系、东亚区域史与世界史的关系等问题。池本幸生在研讨会上联系阿玛蒂亚·森《正义的理念》一书中的观点,对日本目前面临的危机加以讨论。会议期间,他还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文汇报》记者专访。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徐静波教授对本文亦有帮助)
重要的是GDP增长能不能帮助人们获得更广泛的基本权利
文汇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如今,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方面,中国已经赶超日本,也因此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日本公众、尤其是日本媒体针对GDP总量世界排名的变动有怎样的反应?
池本幸生:日本拱手让出了长期以来GDP总量世界第二的位置,此事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应该说,对日本国民而言,这的确是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GDP总量排名的变化在日本被广泛报道。从日本媒体报道的角度看,俨然就是一副日本被中国夺走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宝座的架势。
从我而言,日本当然是要努力提振经济才行,但是,虽然日本还是有想要重回世界GDP第二大国的愿望,可目前看来,这应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吧。
文汇报:在您看来,“GDP总量世界第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标签,对中国或对日本而言,是否真的很重要?
池本幸生:首先,所谓“经济大国”并非只靠GDP这样一个指标来衡量,日本国内的报道,至少在我看来,是有一点煽动竞争意识的企图的。不知道中国方面如何报道现如今GDP方面的辉煌,是否真的如日本的一些外交评论家所言,“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增强了自信”吗?
另一方面,其实在人均GDP上,日本仍然高于中国。可问题在于,不管GDP总量还是人均GDP,都无法直接等同于幸福。日本人均GDP比较高,就可以据此认为日本人比中国人富裕吗?我们不能忽视了,利润只是一种手段,重要的是利润可以去做什么,重要的是GDP增长能不能帮助人们获得更广泛的基本权利。
文汇报:那么,从人的幸福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对GDP抱持怎样的态度?
池本幸生:根据印度裔学者阿玛蒂亚·森的观点,我们不能单方面过度注重GDP总量的统计,而更关键的是要看,人们在这个国家生活时所体会到的幸福的程度。日本虽曾长期保持着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但其实日本人并不是那么幸福。举一些简单的例子:日本总是受到失业率问题的困扰,很多年轻人从大学毕业后都不是那么容易找到工作,总是或多或少面临着就职难的问题;另外,在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的日本,老年人也常常不能及时获得足够的养老金。所以,日本虽然一直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人均GDP比中国高,但其实日本国民的幸福感并不充足。
GDP这个概念造成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差异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以大家熟悉的福岛核电站事故为例。当时,日本国内有一种广受认同的意见,即认为东京地区比福岛地区发达,因此核电站应该选址在相对不发达的福岛。显然,这对福岛的居民来说是不公平的。这是依靠GDP作决定而导致的不公,反过来说,也是为了GDP能有更大提升而造成的不公。
在经济学上,总是以GDP来衡量社会状况的优劣,以GDP增加与否来判断改革方案是否令人满意。森否定了这种思考方式。GDP水平再高,但如果人们是在半强制劳动下获得这种GDP的增长,那么人的自由就会受损,生活的福祉也会恶化。为使社会更合乎正义,森强调民主的重要性。他主张,让大量的人表达自己的意见,是使社会趋近正义的有效手段。
文汇报:一个多世纪前,日本试图脱亚入欧,于是大量引进西方学术、热衷于西方学术思潮;而中国近现代对于西方的认识,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日本。今天,日本的思想界、学术界对西方学术思潮是否依然热衷?
池本幸生:最近日本对西方的学术和思潮都不是非常敏感。如果以翻译西方作品的数量来衡量的话,翻译数量并不多,而且大多数是大众读物,而不是学术著作。
日本国内本土的学术气氛也不浓。老一辈的学者因为精力有限也未必能做下去,而对于年轻人而言,许多学术项目的展开是要有经费预算支撑的,这对年轻学者来讲也是压力重重。
文汇报:您已经把阿玛蒂亚·森的一些著作介绍到日本国内。请问在日本国内,学术界对于阿玛蒂亚·森等学者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及学术观点的接受程度如何?森在日本是一名为人熟知的学者吗?
池本幸生:在日本的情况是这样的:一般的经济学家并不是很喜欢阿玛蒂亚·森,而那些以批判的眼光对待经济学的学者比较能接受森的一些观点。经济学家总是很关注GDP的增长,而森对只注重GDP的这种经济发展观点是持批判态度的。当然,日本国内也有部分经济学家反对经济发展只注重GDP的取向,对于他们而言,森的学术和观点值得推崇和研究。
思考如何去除实际存在的明显的不正义,更具现实意义
文汇报:正义和民主是阿玛蒂亚·森一直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如何理解民主在追求正义过程中的作用?
池本幸生:我的观点是,对正义来说,民主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不应该由一个大人物来决定任何事情。
关于“正义”这个话题,制度主义者认为,所谓正义是要追求合乎正义的制度,正义是可以通过“正确的制度”来实现的。但制度正义的问题在于,让所有人在一种制度上达成一致意见是不可能的,比如,美国、中国和日本可以采取相同制度吗?
相较于这种拘泥于制度的思路,还有一种比较主义的想法,这种想法重视比较现状和现状改变后的结果,如果普遍认为后者比前者更符合期待,社会就会得到改善。亚当·斯密和阿玛蒂亚·森关于正义的观点都属于这个方向。森认为,思考何为完美的制度对于应付现实问题并没有什么帮助;相比之下,更有用、更具现实意义的是思考如何去除实际存在于世间的明显的不正义。因此,森放弃寻求终极正义理论,认为要获得对于正义的解答,只能依赖于理性、民主的讨论。我也完全赞同他的观点。
文汇报:谈到民主,人们总会联想到“一人一票”、“投票制”这类操作方式。您认为民主和选举之间可以简单地等同起来吗?
池本幸生:我们的确可以看到,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选举制,但并不能说,选举制存在的国家和地区,对民主就实践得很好。
有些选举只是看似民主,但并不具备实质上的投票自由。例如,缺乏自己想要支持的候选人的选举、半强制状态下不得不投票给独裁政权推举的候选人的选举、贿选横行的选举,这些都和民主相去甚远。以同样实行选举制的老挝为例,他们的投票率很高,应该已经达到90%以上,但候选人只有一个,投票者并没有其他选择。像这种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又有什么意义呢?在我看来,这样的投票和真正的民主没有什么关系。
反过来讲,有些国家并不实行选举制度,但是如果最高层能够通过适合的渠道听取民众的意见,充分吸纳各阶层的建议,这样不也是有民主成分在其中吗?印度在孔雀王朝时期,也并没有民主选举的制度,但却被认为是很有民主气氛的时期。
民主并非是通过投票之类的制度体现的,而在于民意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于政策。
文汇报:根据经济学的假设,人都是为了追求私利而存在的,人为了他人利益而采取的利他行为被认为是不合理的。但在现实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自私和逐利的人并非没有同情心,并非不懂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和立场考虑问题。从您的研究领域出发,一定也看到在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同情友爱吧?
池本幸生:国际救援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一个国家发生大灾难,当一个国家的人民陷入苦难的时候,其他国家都会及时派出救援力量。这就说明,人类站在他者立场考虑问题的视野正在日益国际化。人在大灾面前表现出的对他人的支援,是基于人类本能的同情,而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利他行为,否则就是对这种同情的亵渎。
确实,从经济活动的过程看,人的确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自然的过程。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阿玛蒂亚·森的作品,就会发现,根据他的观点,人对私利的片面追求并不是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和正确的生活态度。人类还是拥有同情心、利他心和对他人的关怀。人类是怀着对他人的同情、承诺等各种各样的动机,进行选择并作出决定的。这才是真正的人的健康生活状态。我个人也赞同这样的观点。
人类社会中的竞争虽然存在,但不是趋势,人类是向往在平等、协作的社会中生存并进化的。当然,即便认同本能情感的重要性,理性思考也同样重要,因为人们都尽可能通过思考达到客观。
文汇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怜悯、友爱和关怀往往是基于其同样的身份认同。比如,在“311”东日本大地震中,日本国民会基于同胞情谊而互相帮助。与之相对的是,如果身份认同过于强烈,也可能导致国与国之间,不同民族、种族之间出现对立。如何来理解这种基于身份认同的矛盾呢?
池本幸生:人有各种各样的身份,所以也有各种各样的身份认同。比如,我是一个日本人;我居住在东京,所以是东京人;同时,我也是一个男人。在我看来,不管是何种身份认同,至少,我们都是人类的一分子。人类,是一种最大的身份认同。基于这个最大的身份认同,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就可以理解了。
罗尔斯的正义论探究在原始状态下社会成员如何一致接受“社会契约”,这排除了“社会(国家)所有成员”之外的人们,因此带有狭隘性。而要超越这种狭隘性,则必须要有亚当·斯密的“中立的旁观者”的立场,这是一种超越的方法。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谈到“中立的旁观者”这个概念——他人的意见与本人利益直接相关;或虽然与本人无关,但他人的想法可以将讨论引至正确方向。这两种都不可以被忽视。尤其是后者,被称为“开放的中立性”,是超越地域和国家的狭隘性之必需。此外,对他人的同情、承诺和责任的考虑,对超越狭隘性也有重要意义。
媒体避重就轻,导致政府怠于以更积极的姿态应对灾难
文汇报:日本和其他很多国家都在面对一个同样的问题,即媒体在面对各类事情和现象时,缺乏理性的思考和客观的报道。比如您此前提到的媒体对“311”东日本大地震的态度。随着许多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兴起,人们可以通过这些平台更自由地谈论、表达和争辩,话语权不再被垄断。那么,在您看来,新媒体的兴起是否会从客观上促进传统媒体报道的理性的回归?而各种媒体短期内混乱而自由的现状是否会促成今后公共理性的提升?
池本幸生:经过很长时期话语权的分散和自由讨论的氛围熏陶以后,理性的回归也是可以期待的。但是从现阶段来讲,新媒体在提升公共理性方面的作用恰恰是消极的。某种程度上,新媒体可能比传统媒体更加极端和狂热。在日本的“推特”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过激的言论,至少在目前,我完全看不到新媒体在促使理性回归方面的积极意义。
以前在日本,传统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如果有明显的偏见和不客观立场,会有人站出来指责。但是日本现在的时评水准非常差,当有比较大的事件发生时,在主流媒体上发声、评论的人,水平往往参差不齐。当然,很明显的一点是,日本政府的声音历来都不是很响亮,也不是很有影响力。日本社会中的话语权一直在民间,民间的立场一直比政府更强烈。但民间发声的自由度太大,会带来很奇怪的现象。比如,有时候日本发生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可是很多电视节目却会找艺人来对此评论和探讨。所以整体看来,我认为现在日本的评论水准是在下降的。过度的自由并没有带来积极的效果。
文汇报:日本政府的声音一直不如民间强,那么是谁在引导舆论?
池本幸生:民间的舆论并不是指一般老百姓发出的声音,民间的舆论其实主要指的是一些民营媒体的舆论。日本的电视台和报纸都是民营的,比如著名的NHK电视台。民间媒体发布的相关消息和报道对一般老百姓会有很大的影响力。民间的报纸、电视台和电台往往会左右舆论,政府往往是被一部分人在操纵。
文汇报:比如被大型财团操纵?
池本幸生:这个问题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势力。还是以福岛核电站事故为例。建造核电站的前期投入非常高,当然,建造完以后,发电成本会比较低。福岛核电站是由东京电力公司来经营的。现在虽然有民意要求停止核发电,但是做不到,政府没有这样的魄力。
除了已经在核电上的高投入和能够实现低成本发电这两个因素以外,之所以无法停止核电,是因为背后还隐约有一种势力,即希望日本能制造原子弹的极端右翼势力。这种势力也掺合其中,导致日本在核发电的用废问题上有着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局面。
正是因为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核电站事故发生后,东京电力公司的人并未受到处罚,也未被起诉,东京电力公司也没有充分支付对灾民的补偿金。在福岛核电站事故过去那么久之后,政府经过勘测,认为居民可以回到家园生活,可问题是,灾民并没有足够的钱来重建家园。本来,政府应该敦促东京电力公司及时、充分地支付给灾民补偿金,但实际情况是,灾民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
文汇报:媒体的力量和政府的作用都无法体现吗?
池本幸生:某种程度上说,媒体和政府想要忘记福岛。“311”东日本大地震并引发海啸以后,有一定面积的受灾区并未得到有效救援。政府隐瞒了福岛核电事故的危机程度,而媒体也避开了受灾严重的地区,避开了事发地的困境,只是报道政府公告的一些消息。媒体的这种趋向也导致政府怠于以更积极的姿态应对灾难。
一般情况下,媒体应该关注这些灾民,为他们呼吁,然后引起全体国民的关注,并及时给予帮助。报道应该在推进对受灾者的救援上有重要意义。但是,震后日本电视节目中反复播放的是街区被海啸吞没的影像资料,这的确能够让受灾地之外的人们了解灾害的严重程度,可又有多少实际在寻求帮助的人们的声音被广泛报道出来了呢?报道的相关人员只是去了容易去的地方,反复报道那些一般意义上“被期待”的事。其结果是,被报道的地方得到大量救援,而未被报道的地方就自然地被遗忘了。
在福岛核危机之后,时隔不到两年时间,尽管从救援和安置角度讲,日本政府和社会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在现在的日本,福岛已经离开了人们的关注视野。媒体的焦点又回到了东京这样繁华的地方,已经不太报道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后续情况。
文汇报:比起日本民间某些比较极端的思潮,日本本身的政党政治是否也存在极右化倾向?这也是西方和中国目前都比较关注的问题。
池本幸生:确实如此。我们看最近的日本众院选举投票结果中各个政党获得的席位数,自民党这次拿到294票,确实相当多。自民党获得如此多的席位倒也罢了,可令人费解的是,维新会居然也拿到54票,这是一个非常多的票数了。
在日本政坛,粗粗一分,大致两派,美国派和中国派。从目前的投票结果来看,美国派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另外,有关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问题也是如此,一般支持TPP的人都是支持美国的,而这一派力量现在正在增强。总体而言,现在的日本国内是亲美国派压倒了亲中国派。
在2011年,日本东北部发生了震惊世界的“311”大地震。地震引发了福岛核电站事故和日本东北部核危机,但日本政府却避谈灾难的严重程度;此外,由于媒体缺乏对灾区的客观报道,无视政府公告以外的灾区情况,也间接导致一部分海啸袭击地区未得到有效救援。日本政府的虚与委蛇和媒体的片面立场广受批评。
同年,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池本幸生正在翻译印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的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等作品。“311”大地震中危机被人为严重化的状况令他联想到森关于饥荒的理论。虽然一般认为饥荒是因为歉收而导致粮食不足,但森的研究证明,饥荒不仅仅在粮食供给量急剧下降时才会出现,也可能是因为国家的强力干预而使一部分人失去对粮食的索取权,也可能是饥荒发生时部分人未得到关注而得不到国家应对措施的救援。关于饥荒的理论是帮助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研究。在池本幸生看来,日本“311”大地震后的危机中也能隐约看到森的饥荒理论的影子。
经济学家总是很关注GDP的增长,而森对只注重GDP的经济发展观点持批判态度。池本幸生对森的经济学研究取向非常感兴趣,近年来也致力于将森的著作和学术观点介绍到日本国内,尤其关注的是森关于正义和民主的论述。
不久前,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联合主办的第二届FTP三校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三校的20位与会者围绕“世界史/全球史视野中的东亚”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14-21世纪东亚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和国际地位、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东亚与西方的关系、东亚区域史与世界史的关系等问题。池本幸生在研讨会上联系阿玛蒂亚·森《正义的理念》一书中的观点,对日本目前面临的危机加以讨论。会议期间,他还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文汇报》记者专访。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徐静波教授对本文亦有帮助)
重要的是GDP增长能不能帮助人们获得更广泛的基本权利
文汇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如今,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方面,中国已经赶超日本,也因此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日本公众、尤其是日本媒体针对GDP总量世界排名的变动有怎样的反应?
池本幸生:日本拱手让出了长期以来GDP总量世界第二的位置,此事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应该说,对日本国民而言,这的确是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GDP总量排名的变化在日本被广泛报道。从日本媒体报道的角度看,俨然就是一副日本被中国夺走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宝座的架势。
从我而言,日本当然是要努力提振经济才行,但是,虽然日本还是有想要重回世界GDP第二大国的愿望,可目前看来,这应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吧。
文汇报:在您看来,“GDP总量世界第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标签,对中国或对日本而言,是否真的很重要?
池本幸生:首先,所谓“经济大国”并非只靠GDP这样一个指标来衡量,日本国内的报道,至少在我看来,是有一点煽动竞争意识的企图的。不知道中国方面如何报道现如今GDP方面的辉煌,是否真的如日本的一些外交评论家所言,“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增强了自信”吗?
另一方面,其实在人均GDP上,日本仍然高于中国。可问题在于,不管GDP总量还是人均GDP,都无法直接等同于幸福。日本人均GDP比较高,就可以据此认为日本人比中国人富裕吗?我们不能忽视了,利润只是一种手段,重要的是利润可以去做什么,重要的是GDP增长能不能帮助人们获得更广泛的基本权利。
文汇报:那么,从人的幸福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对GDP抱持怎样的态度?
池本幸生:根据印度裔学者阿玛蒂亚·森的观点,我们不能单方面过度注重GDP总量的统计,而更关键的是要看,人们在这个国家生活时所体会到的幸福的程度。日本虽曾长期保持着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但其实日本人并不是那么幸福。举一些简单的例子:日本总是受到失业率问题的困扰,很多年轻人从大学毕业后都不是那么容易找到工作,总是或多或少面临着就职难的问题;另外,在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的日本,老年人也常常不能及时获得足够的养老金。所以,日本虽然一直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人均GDP比中国高,但其实日本国民的幸福感并不充足。
GDP这个概念造成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差异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以大家熟悉的福岛核电站事故为例。当时,日本国内有一种广受认同的意见,即认为东京地区比福岛地区发达,因此核电站应该选址在相对不发达的福岛。显然,这对福岛的居民来说是不公平的。这是依靠GDP作决定而导致的不公,反过来说,也是为了GDP能有更大提升而造成的不公。
在经济学上,总是以GDP来衡量社会状况的优劣,以GDP增加与否来判断改革方案是否令人满意。森否定了这种思考方式。GDP水平再高,但如果人们是在半强制劳动下获得这种GDP的增长,那么人的自由就会受损,生活的福祉也会恶化。为使社会更合乎正义,森强调民主的重要性。他主张,让大量的人表达自己的意见,是使社会趋近正义的有效手段。
文汇报:一个多世纪前,日本试图脱亚入欧,于是大量引进西方学术、热衷于西方学术思潮;而中国近现代对于西方的认识,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日本。今天,日本的思想界、学术界对西方学术思潮是否依然热衷?
池本幸生:最近日本对西方的学术和思潮都不是非常敏感。如果以翻译西方作品的数量来衡量的话,翻译数量并不多,而且大多数是大众读物,而不是学术著作。
日本国内本土的学术气氛也不浓。老一辈的学者因为精力有限也未必能做下去,而对于年轻人而言,许多学术项目的展开是要有经费预算支撑的,这对年轻学者来讲也是压力重重。
文汇报:您已经把阿玛蒂亚·森的一些著作介绍到日本国内。请问在日本国内,学术界对于阿玛蒂亚·森等学者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及学术观点的接受程度如何?森在日本是一名为人熟知的学者吗?
池本幸生:在日本的情况是这样的:一般的经济学家并不是很喜欢阿玛蒂亚·森,而那些以批判的眼光对待经济学的学者比较能接受森的一些观点。经济学家总是很关注GDP的增长,而森对只注重GDP的这种经济发展观点是持批判态度的。当然,日本国内也有部分经济学家反对经济发展只注重GDP的取向,对于他们而言,森的学术和观点值得推崇和研究。
思考如何去除实际存在的明显的不正义,更具现实意义
文汇报:正义和民主是阿玛蒂亚·森一直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如何理解民主在追求正义过程中的作用?
池本幸生:我的观点是,对正义来说,民主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不应该由一个大人物来决定任何事情。
关于“正义”这个话题,制度主义者认为,所谓正义是要追求合乎正义的制度,正义是可以通过“正确的制度”来实现的。但制度正义的问题在于,让所有人在一种制度上达成一致意见是不可能的,比如,美国、中国和日本可以采取相同制度吗?
相较于这种拘泥于制度的思路,还有一种比较主义的想法,这种想法重视比较现状和现状改变后的结果,如果普遍认为后者比前者更符合期待,社会就会得到改善。亚当·斯密和阿玛蒂亚·森关于正义的观点都属于这个方向。森认为,思考何为完美的制度对于应付现实问题并没有什么帮助;相比之下,更有用、更具现实意义的是思考如何去除实际存在于世间的明显的不正义。因此,森放弃寻求终极正义理论,认为要获得对于正义的解答,只能依赖于理性、民主的讨论。我也完全赞同他的观点。
文汇报:谈到民主,人们总会联想到“一人一票”、“投票制”这类操作方式。您认为民主和选举之间可以简单地等同起来吗?
池本幸生:我们的确可以看到,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选举制,但并不能说,选举制存在的国家和地区,对民主就实践得很好。
有些选举只是看似民主,但并不具备实质上的投票自由。例如,缺乏自己想要支持的候选人的选举、半强制状态下不得不投票给独裁政权推举的候选人的选举、贿选横行的选举,这些都和民主相去甚远。以同样实行选举制的老挝为例,他们的投票率很高,应该已经达到90%以上,但候选人只有一个,投票者并没有其他选择。像这种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又有什么意义呢?在我看来,这样的投票和真正的民主没有什么关系。
反过来讲,有些国家并不实行选举制度,但是如果最高层能够通过适合的渠道听取民众的意见,充分吸纳各阶层的建议,这样不也是有民主成分在其中吗?印度在孔雀王朝时期,也并没有民主选举的制度,但却被认为是很有民主气氛的时期。
民主并非是通过投票之类的制度体现的,而在于民意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于政策。
文汇报:根据经济学的假设,人都是为了追求私利而存在的,人为了他人利益而采取的利他行为被认为是不合理的。但在现实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自私和逐利的人并非没有同情心,并非不懂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和立场考虑问题。从您的研究领域出发,一定也看到在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同情友爱吧?
池本幸生:国际救援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一个国家发生大灾难,当一个国家的人民陷入苦难的时候,其他国家都会及时派出救援力量。这就说明,人类站在他者立场考虑问题的视野正在日益国际化。人在大灾面前表现出的对他人的支援,是基于人类本能的同情,而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利他行为,否则就是对这种同情的亵渎。
确实,从经济活动的过程看,人的确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自然的过程。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阿玛蒂亚·森的作品,就会发现,根据他的观点,人对私利的片面追求并不是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和正确的生活态度。人类还是拥有同情心、利他心和对他人的关怀。人类是怀着对他人的同情、承诺等各种各样的动机,进行选择并作出决定的。这才是真正的人的健康生活状态。我个人也赞同这样的观点。
人类社会中的竞争虽然存在,但不是趋势,人类是向往在平等、协作的社会中生存并进化的。当然,即便认同本能情感的重要性,理性思考也同样重要,因为人们都尽可能通过思考达到客观。
文汇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怜悯、友爱和关怀往往是基于其同样的身份认同。比如,在“311”东日本大地震中,日本国民会基于同胞情谊而互相帮助。与之相对的是,如果身份认同过于强烈,也可能导致国与国之间,不同民族、种族之间出现对立。如何来理解这种基于身份认同的矛盾呢?
池本幸生:人有各种各样的身份,所以也有各种各样的身份认同。比如,我是一个日本人;我居住在东京,所以是东京人;同时,我也是一个男人。在我看来,不管是何种身份认同,至少,我们都是人类的一分子。人类,是一种最大的身份认同。基于这个最大的身份认同,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就可以理解了。
罗尔斯的正义论探究在原始状态下社会成员如何一致接受“社会契约”,这排除了“社会(国家)所有成员”之外的人们,因此带有狭隘性。而要超越这种狭隘性,则必须要有亚当·斯密的“中立的旁观者”的立场,这是一种超越的方法。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谈到“中立的旁观者”这个概念——他人的意见与本人利益直接相关;或虽然与本人无关,但他人的想法可以将讨论引至正确方向。这两种都不可以被忽视。尤其是后者,被称为“开放的中立性”,是超越地域和国家的狭隘性之必需。此外,对他人的同情、承诺和责任的考虑,对超越狭隘性也有重要意义。
媒体避重就轻,导致政府怠于以更积极的姿态应对灾难
文汇报:日本和其他很多国家都在面对一个同样的问题,即媒体在面对各类事情和现象时,缺乏理性的思考和客观的报道。比如您此前提到的媒体对“311”东日本大地震的态度。随着许多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兴起,人们可以通过这些平台更自由地谈论、表达和争辩,话语权不再被垄断。那么,在您看来,新媒体的兴起是否会从客观上促进传统媒体报道的理性的回归?而各种媒体短期内混乱而自由的现状是否会促成今后公共理性的提升?
池本幸生:经过很长时期话语权的分散和自由讨论的氛围熏陶以后,理性的回归也是可以期待的。但是从现阶段来讲,新媒体在提升公共理性方面的作用恰恰是消极的。某种程度上,新媒体可能比传统媒体更加极端和狂热。在日本的“推特”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过激的言论,至少在目前,我完全看不到新媒体在促使理性回归方面的积极意义。
以前在日本,传统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如果有明显的偏见和不客观立场,会有人站出来指责。但是日本现在的时评水准非常差,当有比较大的事件发生时,在主流媒体上发声、评论的人,水平往往参差不齐。当然,很明显的一点是,日本政府的声音历来都不是很响亮,也不是很有影响力。日本社会中的话语权一直在民间,民间的立场一直比政府更强烈。但民间发声的自由度太大,会带来很奇怪的现象。比如,有时候日本发生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可是很多电视节目却会找艺人来对此评论和探讨。所以整体看来,我认为现在日本的评论水准是在下降的。过度的自由并没有带来积极的效果。
文汇报:日本政府的声音一直不如民间强,那么是谁在引导舆论?
池本幸生:民间的舆论并不是指一般老百姓发出的声音,民间的舆论其实主要指的是一些民营媒体的舆论。日本的电视台和报纸都是民营的,比如著名的NHK电视台。民间媒体发布的相关消息和报道对一般老百姓会有很大的影响力。民间的报纸、电视台和电台往往会左右舆论,政府往往是被一部分人在操纵。
文汇报:比如被大型财团操纵?
池本幸生:这个问题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势力。还是以福岛核电站事故为例。建造核电站的前期投入非常高,当然,建造完以后,发电成本会比较低。福岛核电站是由东京电力公司来经营的。现在虽然有民意要求停止核发电,但是做不到,政府没有这样的魄力。
除了已经在核电上的高投入和能够实现低成本发电这两个因素以外,之所以无法停止核电,是因为背后还隐约有一种势力,即希望日本能制造原子弹的极端右翼势力。这种势力也掺合其中,导致日本在核发电的用废问题上有着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局面。
正是因为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核电站事故发生后,东京电力公司的人并未受到处罚,也未被起诉,东京电力公司也没有充分支付对灾民的补偿金。在福岛核电站事故过去那么久之后,政府经过勘测,认为居民可以回到家园生活,可问题是,灾民并没有足够的钱来重建家园。本来,政府应该敦促东京电力公司及时、充分地支付给灾民补偿金,但实际情况是,灾民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
文汇报:媒体的力量和政府的作用都无法体现吗?
池本幸生:某种程度上说,媒体和政府想要忘记福岛。“311”东日本大地震并引发海啸以后,有一定面积的受灾区并未得到有效救援。政府隐瞒了福岛核电事故的危机程度,而媒体也避开了受灾严重的地区,避开了事发地的困境,只是报道政府公告的一些消息。媒体的这种趋向也导致政府怠于以更积极的姿态应对灾难。
一般情况下,媒体应该关注这些灾民,为他们呼吁,然后引起全体国民的关注,并及时给予帮助。报道应该在推进对受灾者的救援上有重要意义。但是,震后日本电视节目中反复播放的是街区被海啸吞没的影像资料,这的确能够让受灾地之外的人们了解灾害的严重程度,可又有多少实际在寻求帮助的人们的声音被广泛报道出来了呢?报道的相关人员只是去了容易去的地方,反复报道那些一般意义上“被期待”的事。其结果是,被报道的地方得到大量救援,而未被报道的地方就自然地被遗忘了。
在福岛核危机之后,时隔不到两年时间,尽管从救援和安置角度讲,日本政府和社会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在现在的日本,福岛已经离开了人们的关注视野。媒体的焦点又回到了东京这样繁华的地方,已经不太报道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后续情况。
文汇报:比起日本民间某些比较极端的思潮,日本本身的政党政治是否也存在极右化倾向?这也是西方和中国目前都比较关注的问题。
池本幸生:确实如此。我们看最近的日本众院选举投票结果中各个政党获得的席位数,自民党这次拿到294票,确实相当多。自民党获得如此多的席位倒也罢了,可令人费解的是,维新会居然也拿到54票,这是一个非常多的票数了。
在日本政坛,粗粗一分,大致两派,美国派和中国派。从目前的投票结果来看,美国派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另外,有关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问题也是如此,一般支持TPP的人都是支持美国的,而这一派力量现在正在增强。总体而言,现在的日本国内是亲美国派压倒了亲中国派。
Copyright©2009-2019同济大学医学院关工委 版权所有
